丘逢甲(1864年~1912年)近代诗人。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祖籍嘉应镇平(今广东蕉岭)。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台湾彰化,光绪十四年(1887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登进士(1889年),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强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挂玉钩】迤逦莺啼共燕语,偏向闲庭户。春困佳人睡未足,好梦方惊寤。
淡脸霞,松鬟雾。欲对鸾台,再整妆梳。
【庆宣和】十二帘钩闲控玉,尚掩流苏。嫩寒犹怯透罗襦,绣帏,未出。
【天仙令】晨妆罢,信步向庭隅。晓日楼台,秋千院宇。那更杜鹃催,春事
归欤。怜红爱紫无限心,空自长吁。
【离亭煞】伤春欲待留春住,留春不住随春去。凭谁寄与,问春归去归何处?
只见覆莓苔糁落花,衬榆英铺香絮,又见潋滟池塘涨绿。纵不为五更风,管多因
半夜雨。 秋夜
秋夜谁家砧杵声?不管有人愁听。倦客伤心,披衣独步,踏遍绿苔幽径。
【庆宣和】仙鼠翻风舞画楹,月色偏明。地龙经雨唱空庭,露华,乍冷。
【天仙令】人初静,寂寞旅魂惊。玉宇澄澄,银河耿耿。帘幕夜寒生,月淡
风清。惊鸟绕枝栖未宁,蛩雁哀鸣。
【离亭煞】怯单衣渐觉西风劲,想多情不念东阳病。对景动羁怀,添客恨增
归兴。近玉阑,临金井,早是离人闷哽。桂子散清香,梧桐弄碎影。 悔悟
无限莺花慵管领,恐似沈郎多病。宋玉伤哉,安仁老矣,衰鬓怕临明镜。
【挂玉钩】草草花花一梦惊,断了乔行径。大着多情换寡情,闹里宜寻静。
有况味,无踪影。废尽功夫,误了前程。
【庆宣和】若是自家空藏瓶,梦撒撩丁,花姑不重女猱轻,任谁,见哽。
【天仙令】千金废,火上弄冻凌。他尽是劳成,咱都是志诚。博得个好儿名,
那里施呈。而今纵有双秀才,谁是苏卿?
【离亭煞】早收心拘束定疏狂性,倒大来耳根清净,头轻眼明。跳出面糊盆,
迷魂寨,玻璃井。折莫恁漫天张网罗,遍地剜坑阱,莫想他自家夜行,被你甜句
儿啜来奸,虚脾儿赚得省。
远山,近山,两意冰弦散。行云十二拥翠鬟,搀不定春风幔。锦帐琵琶,司空听惯,险教人唤小蛮。粉残,黛减,正好向灯前看。
锦筝,玉笙,落日平湖净。宝花解语不胜情,翠袖金波莹。苏小堤边,东风一另,怕羞杀林外莺。方酒醒,梦惊,正好向灯前听。
玉舟,渐收,淡淡双蛾皱。鸳鸯罗带几多愁,系不定春风瘦。二八芳年,花开时候,酒添娇月带羞。醉休,睡休,正好向灯前候。
美哉,美哉,忙解阑胸带。鸳鸯枕上口揾腮,直恁么腰肢摆。朦胧笑脸,由他抢白,且宽心权宁耐。姐姐,奶奶,正好向灯前快。
咏美
翠梳,浅铺,粉汁香尘素。画阑谁与月同孤,试听高唐赋。云堆玉梳,多情眉宇,有离人愁万缕。若还,寄取,罗帕上题诗去。
柳腰,翠裙,不似昨宵困。轻风吹散晓窗云,花落佳人鬓。璧月多情,黄昏谁近,素盈盈罗帕尘。泪痕,尚存,须寄与东风信。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丘逢甲
丘逢甲 李白
李白 曾国藩
曾国藩 司马迁
司马迁 柳宗元
柳宗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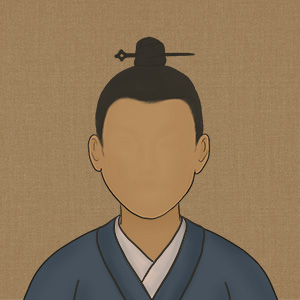 朱庭玉
朱庭玉 张养浩
张养浩 徐灿
徐灿 温庭筠
温庭筠 辛弃疾
辛弃疾 陈允平
陈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