楮亭记
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枳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译文及注释
创作背景
赏析
猜您喜欢
有感
透闺阁,俏名儿都识郑元和。老来犹占排场坐,劝不的哥哥。无钱也怎过活?相识每嗑,推不动花磨。朱颜去了,还再来么?
西湖春晚
系吟船,西湖日日醉花边。倚门不见佳人面,梦断神仙。清明拜扫天,莺声倦,细雨闲庭院。花飞旧粉,苔长新钱。
别情
楚云深,花残月小夜沉沉。五人不见凄凉甚,往事沉吟。香寒茉莉簪,坐冷芙蓉枕,泪淡胭脂添。好因女子,愁似秋心。
分水道中
树槎牙,清溪九曲路三叉。相逢野老别无话,劝早还家。山翁两鬓花,题诗罢,看一幅天然画。炊烟茅舍,晴雪芦花。
透闺阁,俏名儿都识郑元和。老来犹占排场坐,劝不的哥哥。无钱也怎过活?相识每嗑,推不动花磨。朱颜去了,还再来么?
西湖春晚
系吟船,西湖日日醉花边。倚门不见佳人面,梦断神仙。清明拜扫天,莺声倦,细雨闲庭院。花飞旧粉,苔长新钱。
别情
楚云深,花残月小夜沉沉。五人不见凄凉甚,往事沉吟。香寒茉莉簪,坐冷芙蓉枕,泪淡胭脂添。好因女子,愁似秋心。
分水道中
树槎牙,清溪九曲路三叉。相逢野老别无话,劝早还家。山翁两鬓花,题诗罢,看一幅天然画。炊烟茅舍,晴雪芦花。
山中杂书三首
罢手,去休,已落在渊明后。百年心事付沙鸥,更谁是忘机友。洞口渔舟,桥边村酒,这清闲何处有?树头,锦鸠,花外啼春昼。
夜长,未央,盼杀鸡三唱。东华听漏满靴霜,却笑渊明强。月朗禅床,风清鹤帐,梦不到名利场。草堂,暗香,春已到梅梢上。
醉馀,草书,李愿盘谷序。青山一片范宽图,怪我来何暮?鹤骨清瘦,蜗壳蘧庐,得安闲心自足。蹇驴,和酒壶,风雪梅花路。
野景亭
瓜田邵平,草堂杜陵,五柳庄彭泽令。牵牛篱落掩柴荆,犬吠林塘静。树顶蟾明,水面风生,听渔歌三四声。小亭,野景,动著我莼鲈兴。
酸斋席上听胡琴
玉鞭,翠钿,记马上昭君面。一梭银线解冰泉,碎拆俪珠串。雁舞秋烟,莺啼春院,伤心塞草边。醉仙,彩笺,写万里关山怨。
春思
见他,问咱,怎忘了当初话?东风残梦小窗纱,月冷秋千架。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五花,骏马,何处垂杨下。
梅友元帅席上
老夫,病余,尚草《长门赋》。阿莲娇吻贯骊珠,试听《莺啼序》。玉露冰壶,香风琼树,醉归来不用扶。小奴,按舞,看了梅花去。
罢手,去休,已落在渊明后。百年心事付沙鸥,更谁是忘机友。洞口渔舟,桥边村酒,这清闲何处有?树头,锦鸠,花外啼春昼。
夜长,未央,盼杀鸡三唱。东华听漏满靴霜,却笑渊明强。月朗禅床,风清鹤帐,梦不到名利场。草堂,暗香,春已到梅梢上。
醉馀,草书,李愿盘谷序。青山一片范宽图,怪我来何暮?鹤骨清瘦,蜗壳蘧庐,得安闲心自足。蹇驴,和酒壶,风雪梅花路。
野景亭
瓜田邵平,草堂杜陵,五柳庄彭泽令。牵牛篱落掩柴荆,犬吠林塘静。树顶蟾明,水面风生,听渔歌三四声。小亭,野景,动著我莼鲈兴。
酸斋席上听胡琴
玉鞭,翠钿,记马上昭君面。一梭银线解冰泉,碎拆俪珠串。雁舞秋烟,莺啼春院,伤心塞草边。醉仙,彩笺,写万里关山怨。
春思
见他,问咱,怎忘了当初话?东风残梦小窗纱,月冷秋千架。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五花,骏马,何处垂杨下。
梅友元帅席上
老夫,病余,尚草《长门赋》。阿莲娇吻贯骊珠,试听《莺啼序》。玉露冰壶,香风琼树,醉归来不用扶。小奴,按舞,看了梅花去。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推荐诗文
 袁中道
袁中道 辛弃疾
辛弃疾 张可久
张可久 张养浩
张养浩 牛希济
牛希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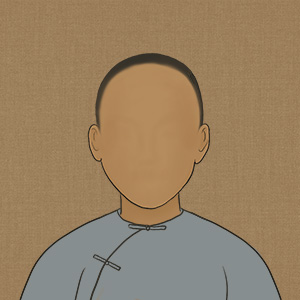 李雯
李雯 韦庄
韦庄 刘禹锡
刘禹锡 苏轼
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