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万柳堂记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
译文及注释
创作背景
赏析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刘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雍正七年(1729年)和雍正十年(1732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刘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论文偶记》1卷,纂修《歙县志》20卷。逝世后,安葬在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文物。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蓴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刘大櫆
刘大櫆 左丘明
左丘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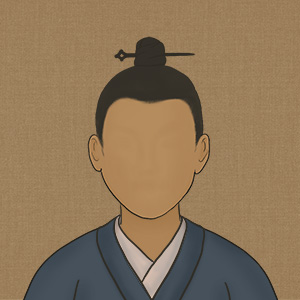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孙道绚
孙道绚 薛昭蕴
薛昭蕴 萨都剌
萨都剌 况周颐
况周颐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温庭筠
温庭筠 辛弃疾
辛弃疾 关注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