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刘老人百一歌
昔闻宁王嘉定时,平淮如掌粮如坻。襄阳高屯十万卒,武昌金埒饶军资。
西蜀环山堆锦绣,滔滔南纪喉襟首。峨眉积雪不动尘,玉垒浮云古今守。
当年行都号全盛,翠箔珠帘争斗胜。西湖不识烽台愁,北关已绝强邻聘。
宝庆天子来自外邸朝诸侯,土疆日窄边庭忧。大帅偃蹇藩镇侔,小垒椎剥租瘢稠。
春城弦管暗烟雨,四十一年变灭同浮沤。咸淳太阿已倒持,铜山之贼专宫帷。
楼危金谷山鬼泣,舸走白浪江神悲。老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帝车书合文轨。
每话承平如梦中,万事东风过马耳。只今行岁一百一,坐阅天地同昨日。
秭归声苦红叶翻,邯郸睡熟黄粱失。门前手种青桐百尺长,笑指截取谐宫商。
少君荒唐方朔诞,不如老人亲见深谷为高岸。我孙之孙为玄孙,翔鸾峙鹄高下飞集骈清门。
凭公欲补先朝事,濡毫更作长生记。
(1266—1327)庆元路鄞县人,字伯长,号清容居士。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成宗大德初,荐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进郊祀十议,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英宗至治元年,官翰林侍讲学士。泰定帝泰定初辞归。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卒谥文清。著有《易说》、《春秋说》、《延祐四明志》、《清容居士集》。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举酒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州。
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韵
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蔽貂裘。
淮头,虏尚虔刘,谁为把中原一战收?问只今人物,岂无安石;且容老子,还访浮丘。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
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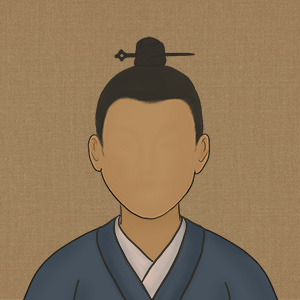 袁桷
袁桷 柳宗元
柳宗元 王安石
王安石 王以宁
王以宁 李曾伯
李曾伯 刘克庄
刘克庄 温庭筠
温庭筠 朱涣
朱涣 毛滂
毛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