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歌行赠栎园道人游武夷
砺君吴刚斫月之玉斧,扬君鲁阳指日之戈殳。饮君邯郸一曲之美酒,赠君绕朝临行之策书。
忆君去年归书绣,高堂燕喜身垂鱼。雕轩列戟侯门屏,金章玉轴照座隅。
词人油素献歌颂,肩軿踵汗仍口呿。青阳逼除才隔岁,南冠顾影行次且。
秋风吹散孟尝客,廉公市门日旰虚。老夫冲寒走问讯,罨头冰雪胶髭须。
溺人但一笑,越吟多嗫嚅。班荆过逢桑下语,仓皇执手临交衢。
且勿赋河梁,且勿歌《骊驹》。听我《放歌行》,请言造化初。
厥初空界二十劫,毗岚橐风吹复嘘。金藏兴云雨如轴,金刚界结胎堪舆。
清水升天淀浊地,七金四洲高下殊。光音天人福报薄,地饼食竭林藤枯。
身光彫落器界暗,四轮墨穴游昏涂。宝音诸地起慈敏,化现日月天地星宫俱。
开张两仪布二曜,二十八宿磊落排空居。梵王口膍脐轮各种族,欲界障持善现相刲屠。
修罗荡脚波海水,生憎头上蹴踏双兔蜍。手幛日轮口啖月,日月怖匿天嗟吁。
此方蚩尤兄弟亦徒党,铜头铁额兴蝥弧。共工触头折天柱,后羿矫矢摧阳乌。
三王五伯迭整顿,君臣将相群拮据。撑天拄地定八极,为此衣冠礼乐争寰区。
东门啸戎索,北落移天枢。裸衣笑神禹,好冠诧勾吴。
退飞未许傍宋鹢,避风何地追鶢鶋。天地为笼逝安适,身藏藕孔难卷舒。
移眉下目吁可怪,闭门捕舌谁能逋。劾君以弹甘蕉之封事,案君以覆郑鹿之追胥。
误君以知雀语之公冶,贵君以辨牛鸣之葛庐。淳于冠缨大笑绝,舍人寠{宀数}居誉呼。
昆山抵鹊用良玉,泉泪洒涕成明珠。心惊蚁床自急捣,梦入鼠穴仍供趋。
斗间干将会须出,山头廷尉当何如。河鼓大星正芒角,横海兵气连无诸。
蛟门水立鸟不渡,子陵滩头断钓渔。老夫已办千日醉,吾子慎爱千金躯。
扁舟东下值元夕,红镫绿酒停姑苏。皋桥银筝裹红泪,迟君拂拭追欢娱。
元墓梅花众香国,西泠红雨桃千株。巾车蜡屐聊复尔,何用䡃辘催奔车。
武夷之君吾远祖,相见遥祝传区区。曾孙面皴头发秃,何当念我诒乾鱼。
酌君酒,揽子袪,我欲竟此曲,此曲烦且纡。咙㗅啽呓如梦魇,宫商失次无疾徐。
征马为踯躅,仆御亦踟蹰。乌啼鸦散君且发,玉壶酒暖还须臾。
放歌行,还须臾。东方瞻顾已精色,晨鸡喔喔鸣前除。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
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
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北辰微闇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
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
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
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帘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皆曰:“如命。”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镜出匣,玉无瑕,在风画图十万家。吃剌剌辗香车,慢腾腾骑俊马。一片飞花,减动西风价。
歌姬程心玉有帘卷新凉之语遂足成之
窈窕娘,淡梳妆,夫容鬓边茉莉香。翠荷觞,锦荔浆。帘卷新凉,人醉西楼上。
越女鸾箫象板,恼司空雾鬓云环。道院弹关,酒会诗坛,万古西湖,天上人间。 钱子云赴都
赋河梁渺渺予怀,今日阳关,明日秦淮。鹏翼风云,龙门波浪,马足尘埃。
宽洗汕胸中四海,便蜚腾天上三台。休等书斋,梅子花开,人在江南,先寄诗来。 江淹寺
紫霜毫是是非非,万古虚名,一梦初回。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
落日外萧山翠微,小桥边古寺残碑。文藻珠玑,醉墨淋淳,何似班超,投却毛锥。 登太和楼
白云中涌出蓬莱,俯视西湖,图画天开。暮雨珠帘,朝云画栋,夜月瑶台。
书籍会三千剑客,管弦声十二金钗。对酒兴杯,拊髀怜才,寄语玲珑,王粲曾来。 竹夫人
湘妃应是前身,不记何年,封虢封秦。万古虚心,百年贞节,一世故人。剖
苍壁寒凝泪痕,挽潜蛟巧结香纹。侍枕知恩,入梦无春,两腋清风,满枕行云。 姑苏台
荒台谁唤姑苏?兵渡西兴,祸起东吴。切齿仇冤,捧心钓饵,尝胆权谋。三
千尺侵云粪土,十万家泣血膏腴。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 名姬玉莲
荆山一片玲珑,分付冯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琼衣露重,粉面冰融。知
造化私加密宠,为风流洗尽娇红。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太华朝云,太液秋风。 春情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
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西湖寻春
清明春色三分,湖上行舟,陌上游人。一片花阴,两行柳影,十里莎ブ。不
要多ゾ排一品,休嫌少酒止三巡。处处开樽,步步寻春。花下归来,带月敲门。 送沙宰
宦游人过钱塘,江水汤汤,山色苍苍。马首西风,鸡声残月,雁影斜阳。男
子志周流四方,循吏心恪守三章。岐麦林桑,渡虎驱蝗。人颂《甘棠》,春满琴
堂。 月
问青天呼酒重倾,几度盈亏,几度阴晴。夜冷鱼沉,山空鹤唳,露滴乌惊。
看杨柳楼心弄影,听梨花树底吹笙。雪与争明,风与双清。玉兔韬光,万古长生。 赠粉英
温柔乡里娉婷,清比梅花,更有余清。玉蕊含香,琼蕤沁月,瑶萼裁冰。冠
杨柳东风媚景,赋芙蓉夜月幽情。花下苏卿,月下崔莺,世上飞琼,天上双成。 西湖夏宴
卷荷筒翠袖生香,忙处投闲,静处寻凉。一片歌声,四围山色,十里湖光。
只此是人间醉乡,更休题天上天堂。老子疏狂,信手新词,赠与秋娘。 红梅
蕊珠宫内琼姬,醉倚东风,谁与更衣?血泪痕深,茜裙香冷,粉面春回。桃
杏色十分可喜,冰霜心一片难移。何处长笛?吹散胭脂,分付春归。
 钱谦益
钱谦益 辛弃疾
辛弃疾 白居易
白居易 佚名
佚名 袁宏道
袁宏道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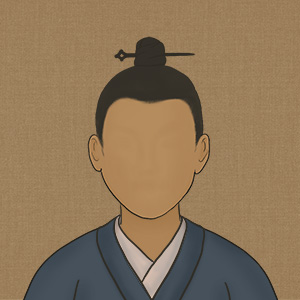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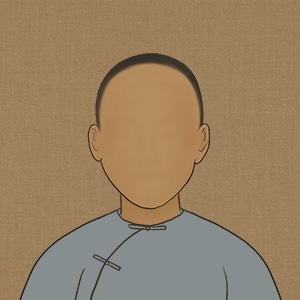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 孙光宪
孙光宪 晏几道
晏几道 温庭筠
温庭筠